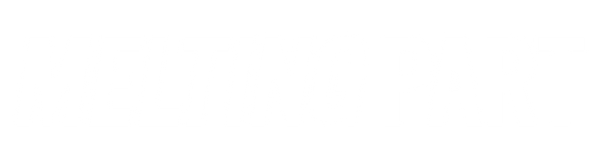Degrees/Interview 專訪 Kamaal Williams: Who is Wu Hen?
Melting Part*本篇訪問內容編撰自2023.1月Kamaal Williams Degrees講座以及Vogue Taiwan專訪

——關於你頭上那頂寫著「吳罕」的帽子,可以說說為什麼會戴著它,以及它的意義呢?
戴著它是想要代表我的血脈,即便只是一頂寫著我中文名字的帽子。而作為一位塗鴉藝術家,書法一直以來都使我著迷,也在我的成長歷程中佔了很大的比重。現在與 Pentagram 的合作過程中,我也確保著這個元素的使用。我的祖母跟母親也都是書法家。因此在結合這些元素的過程,能讓我更能展現我的出身。
——除了吳罕之外,你也自稱Kamaal Williams以及 Henry Wu。這三個名字各自代表什麼?
這三個名字都是我。你知道名字可以用來代表一個藝術家不同的創作身分,這很有趣。我小時候在學校同學都叫我小名「Wu (吳)」,這是我與我的文化背景保持連結的方式。記得放學時母親來學校接我時,同學看到我媽會說原來你是亞洲人,我時常糾正他們我是台灣人。也因此我在2009、2010年開始發行音樂時用的名字是「Henry Wu」。2011年我皈依了伊斯蘭教後,開始自稱Kamaal。在阿拉伯語Kamaal的意思是「完美」,但這不代表我是完美的,比較是追求完美的心態。而Williams則是我父親的姓氏。所有的名字對我來說都很有意義,Henry Wu比較像是個統稱。簡單來說,這有點像你喜歡的導演會偏好和某幾位演員合作,但在每部電影裡這些演員都有不同姓名與人設。像打快旋風一樣,今天你想當Ken另一天當隆(笑)。
——這次你有分享了一張小時候的照片。當中有你的親戚,也有你的祖父母。可以與我們分享你家族的故事嗎?
那是1994年我第一次回到台灣探親時拍的,當時我大概四、五歲。台北帶給我的第一印象極好,簡直是座如夢似幻的城市,與倫敦根本天差地遠。這裡處處充滿著綠色、有著熱帶氣候,在這裡的人們也讓我意識到,這裡就是我的「家」。因為在倫敦,我可以依靠的只有我的母親。母親一直是我的生命旅程中很重要的人物。她是家族中唯一一位離開台灣求學的人,並且在休士頓主修建築學。我聽過很多她作為一位台裔女性身處充滿白人男性的職場環境所受到的歧視,但她總是表現得無所畏懼,更成為了一位成功的建築師。
我覺得我大膽的特質,就是源自我的母親——我的台灣血統。我的祖父母也是個相當有威嚴的人。我記得我第一次與我祖父相遇時,他那強而莊嚴的氣場既讓我害怕,也讓我流在體內的台灣血液感到驕傲。而生為台灣英國混血兒,我一直難與英國文化連結,反倒更能與 Peckham 的西非與牙買加社區產生共鳴。另外就是食物,我的奈及利亞朋友總是說,他們在倫敦如果不是在吃家鄉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吃中菜——畢竟英國食物都沒什麼味道(笑)。我母親在家就是做中式料理,朋友們都搶著要來我們家吃飯。這些都是讓我明白自身與台灣的連結,讓我感到自己是獨特的。
台灣有著寧靜、包容且開放的社群,連我女友第一次來到台北,也無不感受到了台灣人的友善。我的表親也都是這樣的人們。因此我總是有意識地以 Henry Wu(吳)來代表我的身份、我的血統,這是我的責任與義務。

——你的台灣血統一直都存在於創作概念中,是什麼讓你終於決定要來到台灣與在地的場景連結?
事實上,我2017年那次來台就有試圖與一些人聯繫。我當時只待了一週,也並不是那麼的有名,不知道該怎麼與圈內人聯繫。雖然以前在我18歲的時候,我會找機會去一些爵士吧看表演。是直到這五年間我建立起我的身份和作品,讓大家熟悉我之後再與在地人連結。我想也是直到「Wu Hen(吳罕)」這張專輯問世後,大家才知道我其實有台灣的血統。而且說真的,18小時的長途飛行真的不便宜(笑),當時我也沒那麼多錢。所以必須靠探親的假期才能來。現在這個時間點,是我感覺必須要回來的最好時機。終於,我與秋波電台的 Jimmy 聯繫上,也有幸能找到 Michael Ning 和 John Thomas 合作演出。我只能說,拍謝,耗了這麼久。但重要的是我現在來了,我很開心。說起來,河岸留言也是個很棒的場地,還有玉成戲院錄音室,錄音師 Andy Baker 把一個舊戲院打造成很棒的錄音工作室,台灣音樂人真的很幸福,在倫敦都找不到如此美麗的空間。為此,我很期待接下來在這裡的發展,我打算每年回來兩次,希望能做一些常態性的 project。
——台灣普遍認為爵士是比較年長的音樂,請問你怎麼看?
我其實並不稱我的音樂為爵士,也許是因為有許多實體樂器演奏的關係,所以我懂為什麼人們會這麼認為。但我稱我的音樂為 Wu Funk。Wu Funk 確實有受爵士啟發沒錯,其中處處可見爵士的蹤跡,但同時也能從中找到靈魂樂、嘻哈、還有浩室音樂的影子。我本身還是從浩室音樂發跡的,所以如果見過舞台上的我,會發現我的音樂與爵士有距離,甚至很多爵士樂手會說這並不是爵士。如果要為自己的音樂下標語,我會寫——「這不再是爵士了(This ain’t jazz no more)」我透過音樂傳遞的是一個新的世代,以及我的一切。但就理念而言,爵士在五零年代象徵的意義是「自由」「即興」「跳脫框架」與「無畏」,那崇尚反其道而行的精神與我的音樂是相對應的。但就美學而論,並不相同。

——在台灣有許多爵士樂手會替主流藝人伴奏,但卻比較少聽到以爵士為主的主流音樂。你怎麼看待流行音樂產業的爵士樂?
這攸關你如何呈現音樂。你可以不要稱它為爵士。其實我超討厭爵士這個名詞。Miles Davis曾經說過爵士是白人取的名字。定義音樂很難,因為音樂就是音樂。主流音樂當中是有爵士的,譬如Kendrick的第三張專輯《To Pimp a Butterfly》就是爵士。他們也許不被歸類為爵士樂,但你可以說它很 Jazzy。重點是你如何呈現、有沒有故事、如何敘述、有沒有想傳達的理念,那才是重點。爵士永遠不會消失。因為它是最高層級的音樂之一,就好比古典音樂一般。
永遠都會有古典或爵士音樂人不斷創新。像Kraftwerk,他們其實是爵士學院出生的音樂人,但他們創造出跟爵士天壤之別的音樂。創新是關鍵。太多音樂都有人做過,現代人很難創造新的音樂,但我們的優勢是擁有更多的資源。做音樂可以很方便,用筆電就可以取樣(Sample)做出音樂。爵士可以是你的工具跟語言,關鍵是你如何運用它。
——請問你未來有沒有跟台灣音樂人合作的可能?
那是當然的。落日飛車前陣子有在英國布里克斯頓(Brixton)演出,我的所有台灣朋友都有去看,因此認識了他們。9m88 也是,她很棒,充滿著爵士的風味以及漂亮的聲線。還有另一位音樂人李權哲,單憑一首 「Sunny Afternoon」,我就迷上他了。我很希望能與大家合作。稍早前在玉成戲院錄音室,由Melting Part主辦的 Workshop 中,我也有機會與眾多音樂家一起交流,分享音樂想法、討論藝術創作的動力和理念,那一直都是我的目標。對於創作,我一直是個非常靈性的人,那次的 Workshop 是個很美好的經驗。當今的社群媒體讓我們遺忘藝術在精神層面的可貴。
——身為一名跨界音樂人,你個人有與時尚圈合作嗎?
音樂跟時尚的合作是必然的,我也與 LV 的 Virgil Abloh 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我擔任了Virgil 東京SS20大秀的作曲家。Virgil也非常支持我的創作,我的饒舌專輯封面就是他替我設計的,其實我現在戴的圍巾也是 Virgil 的傑作。這條圍巾上面的印花是取材自台灣的花釉藝術。如果你看過 Kid Cudi 在 Saturday Night Live 上演出,他那身充滿印花的裙子,其實是來自台灣的花釉圖案。我透過 Whatsapp 傳給 Virgil 台灣瓷器花釉的參考圖,他再從中找到那件裙子的設計靈感。我很喜歡與 Virgil 的合作,我總是會與他深聊關於根源與認同的話題。
——我們有在你的限時動態看到你去買了書法的用具,你也有在寫書法嗎?
有的,在學中文的同時我會一起練習書法。在學習語言上,雖然是從英文開始,但我也學會了阿拉伯文的讀寫,因此現在面對中文,我有志要將這個語言學好,所以才會去你推薦的那家書法店。
——你的專輯封面也一直都有書法的元素。
是的,我第一張專輯封面的書法是由一位華裔穆斯林-哈吉努爾丁所創作。他是一位將漢字與阿拉伯文結合的書法家。《Black Focus》 (2017) 封面的側邊可以找到他的印章,大家可以看看。Kamaal 以往的專輯封面也是由他操刀。而第三張專輯,也是一趟追溯本源的創作旅程。《Wu Hen》(2020) 這張專輯的發表正逢新冠肺炎肆虐的時期。「武漢」(Wu Han) 開始在出現在全球的新聞標題上,成了讓人聯想到負面的字彙。身為「吳罕」-名字有著相同發音的我,因而決定要讓這張美麗專輯與這個名字連繫,並為之帶來光芒。

——來聊聊你的廠牌 Black Focus
Black Focus 是倫敦 Warp Records 與我簽約所成立的廠牌,它就像是我與合作的創作者們共通願景的延續。他們給予我極大的空間簽下任何我想簽的藝人和決定所有發行的日期。雖說我是在經營廠牌和藝人們,其實也只是為他們指引方向讓他們從中自由發揮。而對於唱片製作更是一個與演奏完全不同但我做得順手的領域,讓我可以幫助像是 Mansur Brown、Yussef Dayes 這些非常傑出的音樂家們發展。Black Focus 旗下也有像是 Steve Spacek 這號傳奇人物,單用 Iphone 做了整張專輯,還有 Ratgrave、Swarvy 等人,以及我自己的專輯、和 Wu Tang re-edits 卡帶...
——Wu-Tang Tape?
2018 年我們在 Bandcamp 發了一張名為 Kamaal Williams vs Wu-Tang 的卡帶。有一位現住紐約,叫 SNIPS 的製作人用我 Henry Wu 的作品 re-edit Wu-Tang 的饒舌人聲並傳給我。收到的當時,我人正在摩洛哥與 Cilvaringz 吃午飯 (RZA 的窗口. 負責 Wu Tang 法律相關事務)。我理所當然地向他提起這個作品,對此他並不以為意,我於是告訴他「我的祖父過去被稱為吳將軍 (General Wu),我的存在就是 Wu 家的血脈,所以如果你們要自稱 Wu-Tang,你至少得聽聽這個。」於是他妥協了,並請我傳給他連結。隔天我們在摩洛哥攝影師 Hassan Hajjaj 的家再次碰面,他便抓著我的肩膀,告訴我他多麽喜歡這個作品,也將它遞給了 RZA,而 RZA 的感想說明了一切- “put it out,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
——你怎麼看待 Black Focus 與 Brownswood Recordings 藝人的不同呢?
我們家的藝人比較厲害(笑)。但對於 Gilles Peterson,我有的是滿滿的敬意。他是一位真誠的音樂愛好者,更是 UK 音樂場景很重要的推手。值得一提的是,我對 Giles Peterson 的認識是在台北開始的。當時我 14 歲,在誠品書店找到 Gilles Peterson in Brazil (2004) 這張音樂選輯。它陪伴了我在台的整個假期,也讓我接著購入了他其他像是 Worldwide 等其他選輯 CD。當我一回到英國,便想著總有一天我要與他認識。幾年後,他就在他的電台節目上播放了我的音樂。 Big ups Giles Peterson。但我還是必須說 Black Focus 的藝人比較傑出,除了 Brownswood Recordings 的 Yussef Kamaal(笑)。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大家庭,It’s all love.
——感覺你總是在視覺上結合各種文化,在音樂創作方面也是嗎?
在我即將發行的專輯《Stings》中,所有的視覺都是由 Pentagram 的 Sascha Lobe 所操刀,以及 Kimberly Lloyd,她參與了幾乎所有的設計、品牌製作等等。因為他們的功勞,所有的海報、周邊等設計,都昇華到了另一個境界。有收錄一首名為「Formosa」(台灣)的歌曲。是依首與台灣提琴手Stephanie Yu的合作,有著五聲音階的旋律及合聲在裡頭—相當東方的聲響。這是我製作這張新專輯的目標,融合更多東方意象,並加入更多旋律性的元素在其中。只要一聽到就會懂的。
——你的音樂時常讓聽眾感受到畫面感,在玉成戲院錄音室對談開始前你也播放了一部短片,可以聊聊電影與你創作的關聯性?
我很愛看電影,從小我母親就會在家播放許多經典電影,如黒澤明、馬丁史柯西斯、王家衛等導演的作品。如果人生是一場戲,我覺得我在做音樂時就是在詮釋我的人生電影。將人生發生的事物用藝術性的方式表現出來,對我來說很重要,就如同我在玉成戲院錄音室播放的短片,那是我們去年在巴黎拍攝的。我認為聲音配合影像,對於當代的音樂或藝術家是一個很強烈、能夠觸動人心的創作方式。我們的人生就是上帝執導的電影。所以每當要表演前、我都會禱告,祈求這場演出可以為我的家人、朋友、以及所以參與者帶來正面的影響,而不單純只是為了演出而演出。除此之外,我當然也很愛影像創作。我最近寫了一部電影,會在接下來幾年進行拍攝,也期待到時能夠來到台灣取景。

Photographed by: Lin ChienWen @MW Studio, Lu Chih Hsien @digital_refugee
Interview and Text: _tarolin, Tsiong Hui Lee (Q&A) and Nicole Lee from Vogue Taiwan
Special Thanks: Nicole Lee and Yu Chen Recording Studio.